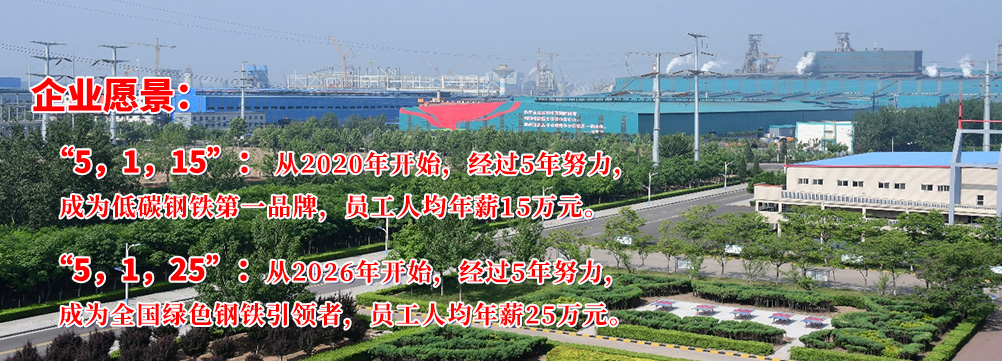化解过剩产能和清退“僵尸企业”,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为何要化解过剩产能的道理不需要我们再赘述。现在,这两项工作已经推进到该落地的时刻,无论是《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脱困发展意见》)还是《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金融支持意见》),以及即将出台的一系列配套政策,都在宣告:化解过剩产能和清理“僵尸企业”的政策窗口和时间窗口已经打开。
纵观几次会议和文件,在强调稳定的同时,都强调此次的去产能并非“一刀切”,要对钢铁企业区别对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脱困发展意见》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标本兼治,《金融支持意见》明确提出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坚持区别对待、有扶有控原则。
现在的问题是,“扶”或“控”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企业属于应该被去产能的那一部分?
很显然,这样一个评价体系不该是简单建立在一份由政府列出的名单之上,也不是简单建立在企业以往的“功劳簿”之上,而应该建立在以法律法规、市场需求、企业发展能力和空间等为主要维度的标准体系之上。据此,以下3类企业应被划归为去产能的对象:一是不合法、不合规的企业,二是市场竞争力难以提高的企业,三是发展空间严重不足的企业。
首先是不符合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企业,以及未经批准建设的企业。
一些环保不达标的钢铁企业已在去年被按日计罚。一些企业通过努力跨过环保“门槛”,另有一些企业仍然认为“罚一天无非相当于卖几吨优质钢”。今后,环保红线必将变成企业即触即亡的“高压电网”,钢铁企业必须保持不可触碰的敬畏心和执行力。
一些安全管理粗放、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应急救援能力不强的钢铁企业仍然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强调,必须坚持安全发展,扎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可以预见的是,市场不能再流通“用生命换来的钢材”,那些没有真正树立起本质安全理念、经过整改也无法迈过“安全线”的企业必须出清。
一些没有履行完整手续、未经批准建设的钢铁企业仍然存在。它们中的大多数在这个钢铁“寒冬”中过得并不好,有的甚至成为扰乱市场秩序、造成区域内产品过剩的根源。对于这类企业理应追查责任。
出清这部分企业的难点在于执法不严。为此,当地相关部门需要加大执法力度,并做好信息公开和备案工作,在必要时,应采取异地执法的手段来避免地方保护,排除其在当地的利益关系对其出清的影响。
其次是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市场竞争力难以提高的企业。
一些不能清偿债务的企业和资产总量已经不足以清偿债务并完成职工安置的企业,虽然没有触碰“红线”,但抓住化解过剩产能的机遇另谋出路不失为明智之举。
一些企业技术装备落后、管理松懈、理念滞后,缺乏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内在基础,被淘汰只是时间问题。
企业应该对资金,尤其是借贷来的资金负责。2015年各月中国钢材价格指数均低于2014年同期,平均值为66.43点,同比下降24.89点,降幅为27.26%。即使如此,我们还是生产了8.038亿吨粗钢。这说明,企业借来的钱并非都变成了改革创新的动力,而是变成了过剩产能。扩量不重质,不仅拖累了自身,还拖垮了市场。
对这些企业,债权人、当地政府和企业自身都不应怀有侥幸心理。投资这样的企业在未来的风险只会越来越大,习惯于得到接济补贴的企业也是饮鸩止渴。这些企业被兼并或被引导退出更有利于其今后的发展。
最后是与区域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或不能融合、企业发展空间严重受限的钢铁企业。
一些城市钢厂的发展已经无法适应其所在城市发展的要求。这些企业的搬迁或停产,要更多考虑有序退出和人员安置的问题。一些内陆钢企受到资源、交通、市场条件等的限制,成本难以下降,企业长期亏损,同样需要审慎考虑其发展方向。
当然,并非所有城市钢厂都与城市发展格格不入,也并非所有内陆钢企都缺乏潜力和空间,但那些对当地区域经济起绝对支撑作用又十分困难、扭亏无望的企业,则很可能成为这次去产能过程中“最难啃的骨头”。对这部分企业来说,政府一定要与企业共同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式。可行的办法是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综合评定,并依据评定指标确定其发展方向。评定指标应既包括高炉停炉/检修时间、吨钢耗能、基础产品成本等技术指标,又包括资金风险、创新能力、社会责任、城市发展相关度等综合经济指标。如果决定继续做钢铁,则应制订细化方案,扎实推进企业扭亏脱困;如果决定转行,则应尽快组织企业诊断,尽快培育新的增长点。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被划归为去产能的对象,必须消除其复产的可能性,必须做好职工安置、清偿债务等各项工作。
地方政府和钢铁企业应该意识到,是否再继续做钢铁,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而是要用企业能否得到更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来判断的。继续生产钢铁未必就好,不再生产钢铁也未必就坏。地方政府和企业领导在做这样的决定时,必须站在全局高度,深入思考、规划地方和企业的未来。